經(jīng)濟觀察報 關(guān)注
2025-04-13 08:52

![](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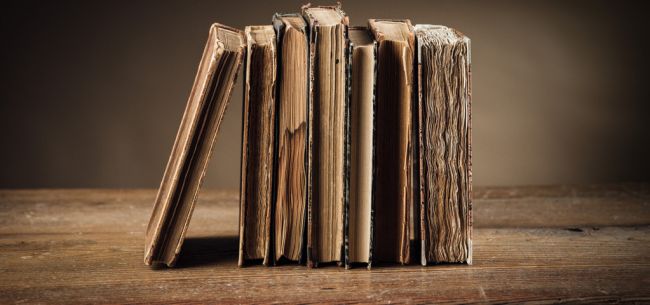
李冬君/文 讀城記:開封型與蘇杭型
傅衣凌在《明清社會經(jīng)濟變遷論》一書中,將中國古代城市分為兩大類型,一類是“開封型”,一類是“蘇杭型”。
下面,我們通過兩幅圖——《清明上河圖》與《姑蘇繁華圖》,來看與之對應(yīng)的文化景觀及其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(xiàn)。
這兩幅圖,一幅是開封圖即《清明上河圖》,一幅是蘇州圖即《姑蘇繁華圖》,從地理位置上看,他們分別位于中原與江南,本來應(yīng)該成為人文地理特征鮮明而迥異的文化景觀,但它們又都處于縱貫?zāi)媳钡拇筮\河帶上,開顯了運河文化樣式的統(tǒng)一性。
此二圖,分屬于不同的歷史時期,一為北宋徽宗時期,一為清朝乾隆時期。在這兩個時期內(nèi),中國都處于歷史的轉(zhuǎn)折點上,承受著不同的歷史周期來自不同方向的歷史的運勢,宋為南北運勢,面對北方?jīng)_擊的馬力,清為東西運勢,面對西方的船堅炮利。
真的不容易,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,不但遭受了草原風(fēng)暴的一次又一次的席卷,還經(jīng)受了一輪又一輪西洋潮的拍打,這個大的歷史周期,經(jīng)歷了好幾個朝代,好幾百年的時間,可結(jié)果呢?朝代一個個倒了,而萌芽還在發(fā)展,發(fā)展出自己的道路。
作為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城市畫卷,兩圖分別描繪了宋代汴京(開封)與清代蘇州的商業(yè)盛景,展現(xiàn)了商品經(jīng)濟從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轉(zhuǎn)型,以及不同階段的市場形態(tài)與文化特征。
以下,從城市商業(yè)結(jié)構(gòu)、行業(yè)多樣性、交通與市場網(wǎng)絡(luò)、廣告與品牌意識、政策與社會影響五個維度對比分析。
我們先來對比一下兩座城市商業(yè)結(jié)構(gòu)的演變。
從《清明上河圖》中,我們看到了北宋時期坊市制的突破與街市繁榮,宋代汴京沿運河分布,打破了唐代“坊市分離”的格局,允許沿街開設(shè)商鋪,形成“街市合一”的開放市場。
圖中,汴河兩岸,商鋪鱗次櫛比,酒樓、茶肆、藥鋪、布店等臨街而立,甚至出現(xiàn)“香豐正店”等豪華酒樓,其彩樓歡門設(shè)計,極具視覺沖擊力,夜市與早市興起,燈箱廣告——如“正店”“腳店”的使用,顯示對商業(yè)活動的時間限制有所松弛。
從《姑蘇繁華圖》中,我們看到了專業(yè)化市鎮(zhèn)與行業(yè)集聚,清代蘇州的商業(yè)布局更趨專業(yè)化。畫中,詳細(xì)描繪了絲綢、棉布、染料、錢莊等行業(yè)的分布,有絲綢店鋪14家、錢莊典當(dāng)14家、洋貨業(yè)2家,顯示了行業(yè)分工細(xì)化與國際化貿(mào)易的萌芽,木瀆鎮(zhèn)、山塘街等市鎮(zhèn)沿運河分布,形成“前店后坊”的產(chǎn)銷一體化。
再來看看兩座城市的行業(yè)多樣性與商品流通。
從《清明上河圖》看汴京民生,可見其日用品與奢侈品并重,既有滿足日需的肉鋪、糧店、茶攤,也有專營弓箭、書畫、珠寶的店鋪,其于餐飲尤盛,既有門面大店,如“孫羊店”等,也有沿街叫賣的小吃攤,遍布于街市各角落。汴河行船,南來北往,川流不息,其貨運之物,不但有糧食,還有絲綢和瓷器。
而從《姑蘇繁華圖》中,則可見清代蘇州手工業(yè)與金融業(yè)聯(lián)動,絲綢、棉紡業(yè)同錢莊、典當(dāng)行攜手,金融資本刺激商品經(jīng)濟,圖中,還出現(xiàn)了洋貨店鋪,如皮貨行、洋貨業(yè),蘇州已然介入全球貿(mào)易網(wǎng)絡(luò),通過大運河下南洋、下西洋,對接國際市場。
所以,還要有交通與市場網(wǎng)絡(luò)確保商品流通。
在《清明上河圖》中,汴河是北宋商品流通的主流通道,圖中船只密集,纖夫拉船,商賈卸貨,可見其樞紐南北,水運繁忙,使之物盡其用,貨暢其流,成為了全國的物流中心。
從《姑蘇繁華圖》中,我們看到了蘇州的經(jīng)濟動脈——大運河與市鎮(zhèn)網(wǎng)絡(luò),清代蘇州依托大運河與太湖水系,形成“木瀆—山塘—閶門”的商業(yè)軸線及其物流。圖中,船只、橋梁、碼頭交錯,近400只船、50余座橋,水陸聯(lián)運,支撐了“百貨駢闐”。
消費主義趨勢的廣告意識和品牌文化隨之興起。
在《清明上河圖》中,“王家紙馬店”“飲子”“香飲子”等招牌清晰可見,商家通過招牌吸引顧客,夜間使用的燈箱廣告(如“正店”“腳店”等),類似現(xiàn)代霓虹燈,顯示品牌意識萌芽。
看《姑蘇繁華圖》,圖中260余家店鋪,如“綢緞行”“布號”“銀樓”等,或以招牌標(biāo)志其營業(yè),或以姓氏、地名前綴為店號,如“陸稿薦”醬肉、“雷允上”藥鋪等,形成“老字號”雛形。另有木瀆鎮(zhèn)、山塘街等市鎮(zhèn),通過運河與蘇州城內(nèi)連接,以市鎮(zhèn)聯(lián)動與跨區(qū)域貿(mào)易,形成專業(yè)化分工,如木瀆以米市、木材交易為主,其品牌突出“漕運”“倉儲”功能,山塘街聚集絲綢、書畫,故其品牌多稱“雅集”“墨韻”,還有14家錢莊、典當(dāng)行,為跨區(qū)域貿(mào)易提供信用支持,商號通過“會票”結(jié)算貨款,促進(jìn)品牌連鎖化經(jīng)營,可見品牌文化中的金融資本效應(yīng)。
若欲深度考察,還得從市場管理上來看一下。
《清明上河圖》,其背景為北宋汴京,市署管理,由官府設(shè)“市易務(wù)”等機構(gòu),監(jiān)管物價、稅收和交易秩序,難免留有坊市制殘余,雖然打破了唐代嚴(yán)格的坊市分隔,但仍有區(qū)域劃分,如御街為商業(yè)主干道,不過,行會已初露端倪,商以行聚,已有“正店”“腳店”之分,但其力量較弱,主要靠官府直接管理。
而《姑蘇繁華圖》,其背景為清代蘇州,市場管理為官民協(xié)作,以行會為主導(dǎo),由絲綢、棉布、錢莊等行業(yè)行會制定行規(guī),控制質(zhì)量、價格和用工,且由市鎮(zhèn)自治,依托宗族與商會,如“洞庭商幫”等,形成半自治的商業(yè)網(wǎng)絡(luò)管理,而官府則通過“牙行”來間接征稅,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(yù),重大糾紛由地方官裁決。
驅(qū)動力:消費驅(qū)動與市場驅(qū)動
我們還可以將這兩幅畫作中的市場管理元素——官方、行會、市集、稅金等,分別提取出來,做進(jìn)一步的對比。
先來看官方元素,在《清明上河圖》中,我們不但可見官署,如“市易務(wù)”等,還可見城門衛(wèi)兵檢查貨物、漕船集中卸貨等,顯示官方對糧食、鹽鐵等戰(zhàn)略物資的壟斷。然而,在《姑蘇繁華圖》中,官府存在感較弱,僅少數(shù)衙役巡邏,稅收通過“牙行”代理。畫中,可見“牙人”——中介,協(xié)調(diào)交易的場景。
再來看行會,在《清明上河圖》中,我們可見商販按行業(yè)聚集,如“孫羊店”酒肆、“趙太丞家”藥鋪等,但無明確行會標(biāo)志,缺乏統(tǒng)一的行業(yè)標(biāo)識,而在《姑蘇繁華圖》中,則行業(yè)標(biāo)識清晰,“綢緞行”“典當(dāng)行”等,由行會制定統(tǒng)一招牌,以“公所”確立質(zhì)量標(biāo)準(zhǔn),圖中出現(xiàn)了行會建筑,如“錢業(yè)會館”。
還有市集元素,在《清明上河圖》中,市集沿街自發(fā)形成,流動性強,存在占道經(jīng)營,如攤販擠占橋梁的現(xiàn)象,糾紛由官府調(diào)解,如圖中可能存在的“訟師”場景等,然而,我們看《姑蘇繁華圖》,則可見市鎮(zhèn)分明,如木瀆米市、閶門絲街等,道路規(guī)整,行會自主調(diào)解糾紛,如“踹布工匠”工資爭議由行會仲裁。
之于稅金方面,從《清明上河圖》里,可見漕運稅糧由官兵押運,商業(yè)稅由市易務(wù)直接征收,貨幣以銅錢為主,然于《姑蘇繁華圖》中,則改以牙行代收,以“會票”信用交易。
若去問一問,導(dǎo)致它們管理差異的深層原因,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政治,由于王安石變法,北宋政府以市易法管理市場,國家干預(yù)的弊端,被畫家張擇端抓住了,將其一一揭示出來,呈現(xiàn)在畫面里,似乎有提醒宋徽宗引以為戒的意思。
清代中央集權(quán),雖不亞于宋,且專制尤甚,但民間社會卻因為走西口、下西洋,而分享了白銀時代的紅利,而有鄉(xiāng)紳與行會崛起,官府間接治理,形成“皇權(quán)不下縣”的格局。
還有,就是經(jīng)濟,北宋經(jīng)濟結(jié)構(gòu),以漕運經(jīng)濟為核心,其商業(yè)帶,分布于汴河兩岸,依附于政治中心——汴京。
因此,《清明上河圖》里的街市場景,不僅帶有明顯的“開封型”的城市化特征,而且其本身就是“開封型”的原型與本尊,其標(biāo)志就是在官府治理下由權(quán)力支配的消費驅(qū)動型城市。
從《清明上河圖》到《姑蘇繁華圖》,它們分別代表了中國古代城市的兩種類型——“開封型”和“蘇杭型”,代表了中國古代經(jīng)濟趨于近代化的兩種典型的經(jīng)濟增長模式——“消費驅(qū)動”與“市場驅(qū)動”,不但顯示了中國經(jīng)濟地理的南北特征,而且反映了中國經(jīng)濟從古代走向近代的歷史進(jìn)程,前者以政治中心的貴族消費為其動力,后者以民間工商業(yè)網(wǎng)絡(luò)的市場擴張為發(fā)展引擎,其消費主體、市場結(jié)構(gòu)、產(chǎn)業(yè)形態(tài)及經(jīng)濟邏輯四方面均有不同。
消費主體的不同,表現(xiàn)為貴族需求與市民經(jīng)濟不同,《清明上河圖》就表現(xiàn)了這種以貴族需求為中心的消費驅(qū)動。
官僚與軍隊消費,可以說是消費驅(qū)動的主力,畫中“正店”“腳店”等高檔酒樓集中服務(wù)于官員、士紳及禁軍,其彩樓歡門設(shè)計彰顯身份區(qū)隔,漕運碼頭的糧倉,如“汴河漕船”,主要為宮廷與軍隊儲備物資。還有消費的奢侈品導(dǎo)向,珠寶行、書畫鋪、香藥局等店鋪,多沿御街分布,商品以奢侈品為主,如“劉家上色沉檀揀香”,依賴貴族階層的文化消費主義的購買力。
而《姑蘇繁華圖》則向我們展示了民生導(dǎo)向的市場驅(qū)動,不僅表現(xiàn)為市民日常消費,體現(xiàn)大眾消費的普惠性,如以畫中“布號”“染坊”與小吃攤、茶館混雜服務(wù)于“百姓日用”,而且表現(xiàn)為跨區(qū)域貿(mào)易的國際化需求旺盛,以錢莊、銀號、典當(dāng)行14家支撐其天南地北、東來西往的大宗商品交易,洋貨行、皮貨行的出現(xiàn),顯示蘇州融入全球市場,消費需求來自國內(nèi)外多層次客戶。
產(chǎn)業(yè)形態(tài)的不同,在此二圖中,表現(xiàn)為中心化的服務(wù)業(yè)集中與去中心的市場化導(dǎo)向的產(chǎn)業(yè)分布式擴張的不同。
于《清明上河圖》中,可見汴京的服務(wù)業(yè)集聚,以漕運經(jīng)濟為主導(dǎo),整個汴京的商業(yè),都圍繞漕運展開,如搬運工、腳店、倉儲業(yè)依附于糧食、鹽鐵運輸?shù)龋瑘D中手工業(yè)均以零散化方式呈現(xiàn),雖有弓箭鋪、鐵器店,但其規(guī)模小,缺乏產(chǎn)業(yè)鏈。
而在《姑蘇繁華圖》中,則可見蘇州對產(chǎn)業(yè)鏈的整合,形成上下游產(chǎn)業(yè)的生產(chǎn)一體化,如在絲綢業(yè)中,就形成了“蠶桑—繅絲—織造—印染”全行業(yè)的生產(chǎn)鏈條,機戶與機工通過雇傭關(guān)系協(xié)作,形成了新的生產(chǎn)方式,以踹布坊、染坊等產(chǎn)業(yè)集聚提升其生產(chǎn)效率。還有金融與實業(yè)聯(lián)動,讓錢莊資本流向生產(chǎn)領(lǐng)域,如放貸給機戶,以此推動技術(shù)升級(如對提花機的改良),實現(xiàn)規(guī)模化擴張。
而經(jīng)濟邏輯的不同,則表現(xiàn)為對分配優(yōu)先還是效率優(yōu)先的選擇,選擇消費驅(qū)動的分配邏輯或市場驅(qū)動的效率邏輯。
汴京的帝都地位,是通過財富再分配來維系的,汴京繁榮依賴于江南稅糧與北方邊疆軍事需求的財富轉(zhuǎn)移,其本質(zhì),乃以政治權(quán)力主導(dǎo)“分配型經(jīng)濟”,這就必然導(dǎo)致其技術(shù)停滯。
而蘇州則采取資源優(yōu)化配置的方式,通過運河整合江南資源,如湖廣糧食、松江棉布等,形成其全國性的分工網(wǎng)絡(luò),并對技術(shù)進(jìn)行適應(yīng)性改良,以應(yīng)對市場需求,如棉紡業(yè)改進(jìn)“三錠紡車”,絲業(yè)優(yōu)化染色工藝(如“一染十色”技術(shù)),顯著提升了效率。
這兩種模式的興衰,給我們以啟示,汴京型消費驅(qū)動,因其過度依賴政治權(quán)力與外部資源輸入,故其繁榮的本質(zhì)是“寄生性增長”,缺乏內(nèi)生動力,若帝都失落,便繁榮不再。而蘇州型市場驅(qū)動,是以民間資本與專業(yè)化分工為基礎(chǔ),即便遭遇戰(zhàn)亂,被太平天國運動席卷,它仍能依托其地理與產(chǎn)業(yè)的韌性復(fù)蘇,成功體現(xiàn)了“生產(chǎn)性增長”的可持續(xù)性。
兩圖,揭示了中國經(jīng)濟的雙重面相:消費驅(qū)動,雖能在行政權(quán)力的加持下,創(chuàng)造短期繁榮,但受制于政治周期。而市場驅(qū)動,則以自發(fā)性的經(jīng)濟成長,為經(jīng)濟發(fā)展提供持久動力。
類型化:彈性社會的城市縮影
“開封型”與“蘇杭型”,分別代表了中國古代城市的兩種典型的類型,在中央集權(quán)的統(tǒng)一治理下,居然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發(fā)展模式——“開封型”政治經(jīng)濟復(fù)合中心與“蘇杭型”工商業(yè)市鎮(zhèn)網(wǎng)絡(luò)。這在體制內(nèi),是以源源不斷的財富轉(zhuǎn)移換來的發(fā)展空間,即便專制制度,有時也要默認(rèn)“自由補償”的原則。
于是,我們看到了兩種不一樣的城市功能:一個作為政治中心——“開封型”,一個作為經(jīng)濟樞紐——“蘇杭型”。
開封作為北宋都城,是國家軍政漕運中心,體現(xiàn)了政治主導(dǎo)功能,商業(yè)活動依附于政治需求,商鋪營業(yè)多沿御街分布,服務(wù)于官僚階層與軍隊,市場繁榮其表,官方管控其內(nèi)。
而蘇州作為一座由市場驅(qū)動的工商業(yè)城市,以絲綢、棉布、金融業(yè)為核心,依托運河與太湖,形成木瀆、山塘等專業(yè)化市鎮(zhèn),以其市鎮(zhèn)網(wǎng)絡(luò)聯(lián)動,經(jīng)濟輻射長江三角洲乃至海外。
城市的空間結(jié)構(gòu)也表現(xiàn)出兩種類型,一種是中心化的,基于頂層設(shè)計而成就的軸線規(guī)整的都城,一種是去中心的,由水網(wǎng)縱橫,水陸并行,順其自然而形成的“水陸雙棋盤”格局。
汴京,以御街為中軸,宮城、官署、市集依次排列,體現(xiàn)“前朝后市”的傳統(tǒng)禮制,城墻與坊市分隔,盡管打破唐代坊市制,但仍可見城墻、坊門遺跡,商業(yè)區(qū)集中于汴河沿岸。
蘇州,以河道為城市骨架,街巷沿水展開,以小橋流水串聯(lián)運河,浮現(xiàn)水鄉(xiāng)肌理,流通水城地脈。城中橋梁密布,船只穿梭,碼頭裝卸繁忙,市鎮(zhèn)散點分布,市集隨運河擴散,如木瀆鎮(zhèn)以米市聞名,閶門以絲綢貿(mào)易為主,表現(xiàn)為多中心結(jié)構(gòu)。
還有不一樣的經(jīng)濟,作為了城市的集中表現(xiàn)。“開封型”經(jīng)濟,由官方主導(dǎo),以官商結(jié)合,形成漕運經(jīng)濟,而“蘇杭型”經(jīng)濟,由民間自發(fā),民生主導(dǎo),自主經(jīng)營,形成市場經(jīng)濟。
汴河作為漕運經(jīng)濟生命線,運輸江南稅糧與官營物資,如以“綱船”運鹽,街市運營,由官方授予特許經(jīng)營權(quán),一些酒肆、茶坊,需經(jīng)官方授權(quán)方能成為“正店”,商人依附權(quán)貴,竟然成為招牌,如“趙太丞家”藥鋪,顯示其有官商背景。
而在“蘇杭型”市場網(wǎng)絡(luò)中,則不但可見民營手工業(yè)集群式發(fā)展,絲綢業(yè)“機戶出資,機工出力”形成雇傭勞動關(guān)系,棉布業(yè)以“放料收布”模式連接城鄉(xiāng),還可見金融資本活躍,錢莊、典當(dāng)行支持跨區(qū)域貿(mào)易,推動信用經(jīng)濟,如以“會票”交易。
文化的表現(xiàn),也呈現(xiàn)出了不同的景觀,“開封型”的文化是官文化,矗立起官本位的禮制威嚴(yán),“蘇杭型”為民文化,在市場經(jīng)濟里,以其市民文化,如流水載舟,載以民生。
開封城建筑恢弘,城門、鐘鼓樓等,一一彰顯皇權(quán),即便“瓦舍勾欄”,談天說地于市井間,說的也是忠義,作為國際都會,在御街上,亦可見駱駝商隊,留下一路朝貢的話語。
而蘇州,則出現(xiàn)了市民審美的新文藝,園林、評彈、昆曲,煙雨般彌漫于江南的民生里,玉潤于水磨調(diào)式的詩畫長河中,淡淡地化為了一種市民悠然的“浮生”雅趣,加以商業(yè)化的新樣式,店鋪賣點綴以“蘇樣”“蘇意”,萌芽了“陸稿薦”“雷允上”等品牌意識,加以市招、燈謎、廟會成就其浮世繪。
這兩幅圖,不僅記錄了中國古代城市的多樣性,更揭示了不同發(fā)展路徑的歷史命運——政治中心的榮耀易逝,市場經(jīng)濟的活力長存。如此對比,也為當(dāng)代城市規(guī)劃提供了啟示:可持續(xù)的城市生命力,根植于民間經(jīng)濟的自發(fā)性與文化的在地性。
傅衣凌的“開封型”與“蘇杭型”城市理論,不光是對中國傳統(tǒng)城市經(jīng)濟的類型學(xué)劃分,更是對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“彈性結(jié)構(gòu)”的城市化解讀,成為了“彈性社會”濃縮的一個縮影。
傅衣凌認(rèn)為,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是個“彈性社會”,其具體表現(xiàn)為經(jīng)濟結(jié)構(gòu)的“膠著性”和階級關(guān)系的“彈性捆綁”。
總起來說,有“三個膠著”,有“兩大捆綁”。
中國古代社會經(jīng)濟,存在三對“膠著”關(guān)系:
一是自然經(jīng)濟與商品經(jīng)濟膠著,商品經(jīng)濟發(fā)展兼容自然經(jīng)濟——“以末求富,以本守之”,讓“死的拖住活的”。
二是土地運動的相對自由與穩(wěn)定性膠著,土地雖可買賣,但受鄉(xiāng)族與國家共同體制約,導(dǎo)致私人所有權(quán)不完整。
三是區(qū)域發(fā)展不均衡膠著,先進(jìn)地區(qū)與落后地區(qū),通過國家政策與人口流動,維持其動態(tài)平衡,抑制整體突破。
而“彈性社會”運行,也以“膠著”方式,表現(xiàn)為“公”與“私”的“膠著”。“公”為國家政權(quán),“私”為鄉(xiāng)族勢力,其互動——中央集權(quán)與鄉(xiāng)族自治,也“膠著”在一起,既合作又分離,在大一統(tǒng)的政治追求中,又不得不采取“公私共治”。
其階級性與鄉(xiāng)族性并行,帶來“兩大捆綁”:
一是鄉(xiāng)紳與農(nóng)民利害捆綁:鄉(xiāng)族勢力既維護(hù)地主利益,又以義莊、族田緩和階級沖突,形成“溫情脈脈的剝削”。
二是身份流動與制度固化:科舉制引導(dǎo)階層流動,但官僚體系卻與土地權(quán)力結(jié)合,使商人依附舊體制,難以獨立。
國家與鄉(xiāng)族共治,具有多元權(quán)力結(jié)構(gòu)的韌性,形成“政權(quán)、紳權(quán)、族權(quán)、神權(quán)”綜合體,超經(jīng)濟強制與經(jīng)濟強制交織,地租剝削與人身依附并存,抑制了資本主義萌芽,使之陷入“夭折機制”,既受制于技術(shù)停滯,又被制度反制,且以政策限制,讓資本回流于土地,回到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的蓄水池,進(jìn)入一個制度化和社會化的“寄生性資本循環(huán)”,走不出“彈性社會”。
傅衣凌指出,這樣的歷史表現(xiàn),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長期延續(xù)的根源。這一理論,雖被人稱之為“自梁啟超‘近世’概念后,是對中國近代史最精辟的詮釋”,但我們認(rèn)為,這還不夠,還應(yīng)當(dāng)把“彈性社會”放到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的互動關(guān)系中來解讀,把它當(dāng)作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的“結(jié)合部”來看。
我們認(rèn)為,傅衣凌的“彈性社會”說,本質(zhì)上揭示了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的對立統(tǒng)一,作為“結(jié)合部”,它不但依附于王朝中國的制度安排,而且附著于文化中國的機體成長,因而,既是傳統(tǒng)社會長期穩(wěn)定的根源,也是近代化轉(zhuǎn)型滯后的關(guān)鍵。
在此語境下,“彈性社會”理論,不僅為理解中國道路提供了歷史縱深,也為制度與文化協(xié)同創(chuàng)新指引了可能性的路徑,正如費孝通所言,中國社會結(jié)構(gòu),如“差序格局”般層層推衍,而“彈性社會”正是這一格局中權(quán)力與文化交織的動態(tài)呈現(xiàn)。
(作者近著:《走進(jìn)宋畫——10—13世紀(jì)的中國文藝復(fù)興》,北京時代華文書局)
?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 11010802028547號
京公網(wǎng)安備 11010802028547號